到农村你最不能忍的是什么?
打工仔年三十回家,开一个破旧小车,新车10W
级,残值5-6W。
小学同学,没读大学,甚至高中都没读的一般子同
学。家门口是奥迪A4、Q5,奔驰GLC、大众途
昂、保时捷等。
我三十才回家,而他们已经回家一星期了。我初六
赶回单位上班,他们说要过完十五再出去。不敢同
他们打牌,输赢太大,背不住。回避他们的吃喝宴
请,经济上差距太明显!
村里凡是上过大学的,无论是博士,硕士还是本科, 过年回家都很安静;而那些早早外出打工的,却表现的很热情。 年夜饭的圆桌上,两个世界正在割裂。 大学生们低头扒饭,手机屏幕在红灯笼下泛着冷光;打工归来的发小们却端着酒盅满屋转悠,把陈年糗事说得满屋哄笑。 这样极具魔幻主义色彩,现实主义的春节图景, 正在中国无数村庄悄然上演。 教育这架社会阶梯在向上输送知识精英的同时, 也在故乡的土地上划出深邃的裂痕和隐性的鸿沟。 文明正在成为知识分子的枷锁吗?
当演讲竞赛时侃侃而谈的大学生,在面对大姑“读这么多书有啥用”的质问却瞬间失语;当论文答辩时滔滔不绝的硕士生,在面对二婶儿“怎么学越上话越少,书越读人越呆”的轻声吐槽时惊慌到即使生气而又无力反驳;当能在学术论坛舌战群儒的博士生,被三叔公”每月挣多少钱?"的关切时,措不及防之下,心理防线瞬间崩塌..... 一个个既真实而痛苦的对话,一个个无能为力的瞬间,让无数大学生,深切感受到文化身份的撕裂, 和精神的质疑失语。 心里知道,他们既无法完全认同城市白领的消费主义,而我们又难以回归乡村的宗族伦理。
当中存在着两种认知和主导系统的对抗,一个是以大学生等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知识构建的认知体系,一个是以家乡当地人和返乡务工人员为主体的乡村经验主义的话语系统。 这两种孕育在不同环境中,起着不同作用的话语体系随着春节的到来,在年夜的饭桌上,在走亲访友的交谈中.... 它们相遇,激烈碰撞,在以乡土文化为土壤,人情世故为主场的家乡,显然后者更胜一筹,仿佛在我们眼里呈现出一种,不知是真还是假的现象, 即“高等教育正在批量生产新型“哑巴”。 当母亲炫耀“我家娃在写SCI论文”时,邻居却更关心打工青年新买的轿车。
上一篇:何为忠诚!
下一篇:不同阶层都在干什么

 励志语录
励志语录 励志名言
励志名言 经典语录
经典语录 励志口号
励志口号 经典台词
经典台词 立志语录
立志语录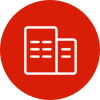 励志文案
励志文案 励志文章
励志文章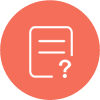 励志故事
励志故事 网站首页
网站首页